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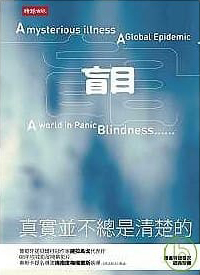
作者介紹
喬賽‧薩拉馬戈(Jose Saramago)1922年生於葡萄牙,曾經操持多種不同行業已維生計,包括技工、技術設計人員與文學編輯,但是他從 1979 年起,即全力投入創作。他的作品包含了戲劇、詩作、短篇故事、非小說與虛構小說,他的小說已經被翻譯為二十餘種語言。1988 年出版的《巴達薩與布莉穆妲》(Baltasar and Blimunda)首度將他帶進英語出版世界的焦點,《費城詢問報》(Philodelphia Inquirer)讚美該部小說「一部虛構而極富原創性的歷史小說,足以比美賈西亞‧馬奎斯顛峰時期作品」。薩拉馬戈並以《詩人雷伊斯逝世的那一年》(The year of the Death of Ricardo Reis)一書獲英國《獨立報》(Independent)「國外小說創作獎」;本書譯者喬凡尼‧龐提耶若(Giovanni Pontiero)亦因翻譯翻譯《耶穌基督的福音》(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Christ)一書獲頒 Teixeira-Gomes 葡萄牙語翻譯獎。喬賽‧薩拉馬戈在 1992 年獲選為當年的葡萄牙文作家,並於 1998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,為當今全球最知名的葡萄牙作家,現居加納利群島。
閱讀短文,分項回答下列問題
雪中送炭的好心人幫突然失明盲人把他的車開回家,他說:「要不要我幫你安頓安頓,陪你等你太太回來?」這番熱心忽然讓盲人起了疑,他當然不要請一個素昧平生的人進屋來。天知道他是否此刻正計算著如何制服這個手無寸鐵的可憐盲人,把他五花大綁、封了嘴、洗劫一切物品。不用了別麻煩。他說:「我很好」一面關門一面叨叨念著「不用、不用」。第二天盲人的太太發現丈夫口中的善心人已將車子偷走。
偷車賊提議送盲人回家時並沒有惡意,相反地,他不過是聽從了內心中寬宏與利他的情操。誰都知道「寬宏與利他」是人性裡最美好的兩個特質,即便在比這個小偷冷血得多的罪犯身上也能找到。這人不過是個單純的偷車賊,他承受著真正掌管這項產業的大老闆剝削,毫無希望在事業裡有更上層樓的發展。那些大老闆才是真正占窮人便宜的人。若是為了搶劫而幫助盲人,說穿了,和為了遺產而照顧行動不便、說話結巴的獨眼老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。但他是直到接近了盲人的家時,才自然而然興起了偷車這個念頭,可以說就和看到了彩券攤才決定買彩券是完全相同的道理。他並沒有預感,只是買張彩券來看看會如何,預先服從了變幻莫測的命運所可能帶來或不帶來的東西。但也可以說他的行為是一種性格下的制約反應。論起人性,為數眾多且頑固不化的懷疑論者宣稱,即使小偷不完全是機會的產物,機會也的確對小偷的塑造貢獻良多。至於我們,則該欣然相信倘使盲人接受了偷車賊的第二個提議,最後人性的寬宏終會得勝。我們說的是陪他等妻子回來的那個提議,誰知道他人賦予的信賴所產生的道德責任不會遏止犯罪的誘惑、讓即便在至為墮落的靈魂中,也能找到的輝煌高貴情操來戰勝一切呢。
問題一:作者認為偷車賊偷車的原因是什麼?他以何事為喻來說明?文長限120字。
問題二:Felson和Clarke的「新機會犯罪理論」,認為人的行為是個人特質與外在場域互動的結果,犯罪機會與個人因素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。請依據本文內容並結合個人的所見所聞,針對「他人賦予信賴所產生的道德責任,能遏止犯罪誘惑」表達你的看法。文長限500字。(不用訂題)
教學文章由景美女中 黃淑偵老師提供
喬賽.薩拉馬戈《盲目》
本書是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在1995年發表的作品。敘述突如其來的傳染病,讓社會陷入人們染疫後就會失明的荒謬境地。故事開始於一個開車者(本書人物都沒有名字)在繁忙的路口突然眼盲而無法動彈,接著被稱為「白禍」的失明症快速蔓延,城市陷入一片混亂。於是,政府當局下令將所有的盲者拘禁於一間精神病院,由武裝士兵看守,然而士兵卻在恐懼與慌亂中開槍狙殺病患。此時,罪惡的因子也在倖存的盲者中萌芽,爭執、搶奪、猜忌,弱者的糧食被偷走,無辜的婦女遭強暴。主角是一名醫生太太,她是唯一保有視力的人,為了照顧失明的丈夫,只好假裝自己也失明一同住院,漸漸因為比他人更清楚狀況而被推向領袖之路,帶領著這些盲人抵抗強盜的侵犯,最後的結局卻出人意料…
作者薩拉馬戈如對這部幫他戴上桂冠極富哲理意涵的傑作曾說:「盲目並非真的盲目,這是對理性的盲目。我們都是理性的人,但是沒有理性的行為。」因此什麼是理性呢?道德是天性還是理性?它的價值與意義會隨著視力的存在與否而改變嗎?讓我們隨著作者進入此書,一起辯證與思索。
首先是對道德與文明的辯證:當代究竟是倚靠甚麼維繫著社會運作?當人們瞬間喪失視力、毫無謀生能力,食物變成彼此掠奪的目標,以腐爛食物果腹﹐從熟食變成生食,被視為文明象徵的「火」,在生活中終將消逝,「生火」是浪費時間沒有必要的事,維持「不吃嗟來之食」的尊嚴,更顯得毫無意義。原本存著寬宏與利他的心態去幫助弱者的偷車賊,在沒有他人注視下突然萌生作惡的念頭,善與惡的分界如此隨機而無法掌握。存在主義學者薩特曾有這樣的名言「他人即地獄」,意即我的世界因他人的存在而混雜,在「他人的注視」下我被物化,為了迎合他人對我的注視,我必須壓抑自我以成為別人認定的那個「我」。那麼當盲症使「注視」不復存在,人的姓名不代表任何意義時,崩毀的除了社會秩序,還有人們逐漸改變的自我價值與認同!但讀者仍不禁要問彼眾昏之日是否有獨醒之人?主角是否能堅持「不愧屋漏」「不欺暗室」的道德理想呢?這也絕對是本書引人入勝處之一。
其次是對真實與相信的辯證:病患眼前一片白茫,究竟能夠相信什麼?聲稱照顧百姓的政府武力囚禁病患,以為來送餐的士兵轉眼瘋狂槍殺病患;三言兩語的交談可以使萍水相逢的盲者成為莫逆之交;此時是共同對抗強盜的同伴,下一刻可能就會為了生存而彼此背叛。「以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,真相總必須偽裝成錯誤才能達到目的。」人們紛紛表示自己失明,以避免外出或搭乘交通工具,聽說有人住在收銀機下,以便恢復視力時可以奪取金錢。這些盲者所有的訊息都來自於道聽塗說,但相信就等於真實嗎?當能夠確定的事情少之又少,最後連宗教信仰都會產生動搖,「神明沒有資格看見東西」群眾破壞神明塑像不只是宣洩,更像是一種末日情境下崩潰的宣戰。
這部25年前完成的作品,今日讀來卻如此地貼近當下情境,回顧這兩年受到新冠病毒衝擊的世界情勢,有搶購口罩民生物資的社會亂象,也有國際之間彼此贈送口罩與疫苗的友好外交,有鄰里集體封住染疫者家門的駭人聽聞,也有志願到醫院工作的護理人員,米蘭昆德拉曾說:「小說家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預言家,他是存在的勘探者。」本書所描繪災難下的人性是蒙塵遭垢還是熠熠閃著銀光?書中許多隱喻例如沒有姓名的角色、消逝的火、埋葬的意義、殺人的道德、英雄的結局、更留待讀者細細思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