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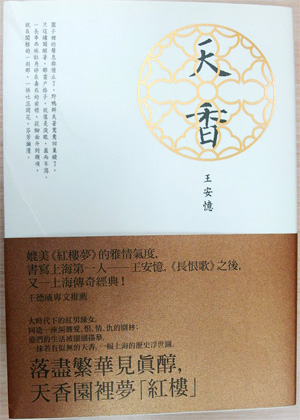
京派和海派是民國白話文學以來,兩個風格迥異的文學派別,造成二者筆觸判然二分的原因固然眾多,梳理後其根源可以用「文化差異」一語貫之。京派作家自詡古都的恬淡,涵養了文人務實而和美的審美情味;海派作家則認為十里洋場的兒女情懷,才是他們騷動心靈的浪漫所在。兩派作家安身立命的北京和上海,就成了最易區辨二者的當代文學史詞彙。
知名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認為:王安憶是繼張愛玲之後,最重要的「海派」文學傳人。王安憶本人則有不同的看法,他認為張愛玲建構的是一個末世,世間人生總是在走下坡路,而王安憶本人則想呈現一個朗朗乾坤的世界,以寫實的故事,構築出一個往上的道途。《天香》一書正展現了王安憶自剖的風格,上海申家所有的天香林園,瀰漫出一派晚明的華靡氣象,申家公子以銀兩雕琢出名流士紳的風雅,只是再華貴的牡丹也會落土,申家敗象漸顯。所幸天香園裡的女性,以其精湛的繡藝,繡出了生命真正的風采,甚至收閭里貧女為徒,讓整個上海都飛滿了纖纖玉腕下精繡的榮華,申家女性開創了上海顧繡的光榮史。在《天香》一書裡,王安憶以筆為針,一線線勾勒出晚明雅緻的上海,也為那群無名的女性,書寫出自開自美的生命力度。
王安憶的父親是話劇作家、導演王嘯平;母親是女作家茹志鵑。王安憶是次女,生於南京,1955年隨母移居上海市,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學,1967年入向明中學讀初中,文革期間曾經秘密地閱讀翻譯的外國著作。1970年,王安憶到安徽省五河農村插隊落戶,1972年考入江蘇省徐州地區文工團,在樂隊拉大提琴,並開始小說創作活動。1976年,王安憶開始發表作品。1978年,王安憶調回上海,擔任中國福利會《兒童時代》編輯,1980年入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。1987年,王安憶調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,從事專業創作,之後擔任中國作協理事、上海作協副主席。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、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。(作家生平改寫自105.03.22維基百科)
四十一、〈登門〉
蕙蘭 想得到又想不到的是,嬸嬸希昭 竟真的上門來了。午後時分,一頂藍布小轎停在臨街的門前,轎夫打起轎帘,希昭出得轎來。身穿靛青裙衫,裙幅上是同色線繡木槿花,冷眼看不出花樣,但覺著絲光熠熠,倏忽間,那花朵枝葉便浮凸出来,華美異常。日頭未有一點偏移,正正地照下來,讓人目眩,於是希昭抬手檔了檔,髮髻上的鳳頭釵搖曳一下,發出清泠的叮噹聲。就有一種窈窕,不是從她身上,而是在她周遭的空氣裡,生出来。希昭舉手叩了門,出來應門的是夫人 ,一時上瞠目結舌,說不出話來。等希昭深深一揖起来,方才喚一聲:嬸嬸來了!蕙蘭在東屋聽到動靜,針都刺了手,忙不迭跑出来,希昭已走到院子中央。正是仲夏時節,院裡的木槿在開花,美人蕉也開花,女貞長了一人半高,枝葉稠密,桂花樹,香樟樹全是新綠幢幢,將院子擠得更逼仄,卻又十分繁榮。希昭好似從花叢中走過,一頭一身的亮和影。夫人將貴客引到廳堂,蕙蘭尾隨身後。婆媳二人全是悽惶的神色,只當是問罪的人來了。希昭轉身看見,不由微微一笑。夫人依次問親家人平安,希昭一一回答都好。夫人略定下神,就喚戥子 上茶,話一出口就覺不妥,收也收不回了。戥子應聲端茶過來,看是二太太,想退也退不下,硬著頭皮上前,放下茶碗逃也似地跑走,很失裡儀,蕙蘭不由滿臉羞紅。見一家上下侷促不安,希昭又一回想笑,但怕夫人見怪,忍住了,垂下眼睛喝茶。喝一會茶,道明來意:聽說蕙蘭侄女繡了一幅新品,是用頭髮辟絲繡成,百聞不如一見,所以按捺不下,直接就跑來了!行動魯莽,请親家母見諒。夫人說:哪裡的話,請也請不來的,實在是喜出望外,’這才亂了手腳,讓親家嬸嬸見笑。說話時,蕙蘭就去取來髮繡。已從繃上卸下,隔了棉紙捲起,裝入錦盒,等畏兀兒來取。
夫人早知道這嬸侄二人情義不同一般,又像是母女,又像是姐妹,當有無數體己話要說,藉口晌午有一眠進屋内去,由她們自去紛爭協調。蕙蘭移開茶盤,解開錦盒,取出繡品,鋪在案上,將棉紙一揭,大佛小佛活脱跳出。希昭俯身看一時,又讓遠了再看一時,看了針跡,又看絲路,至上至下,至左至右,足有半個時辰。兩人都不說話,默著,任由日光挾著花影從繡卷上從東到西。希昭終於看完,說出一聲:果真不凡!蕙蘭不由吁出一口長氣,說道:為嬸嬸這句話,這會兒就死也值得!希昭斜她一眼:莫高興過早,還有不中聽的在後頭!蕙蘭眼睛又睜大了,希昭看她一眼,心中不落忍得很,輕嘆一聲:好,好得很,把心放回肚子裡去吧!蕙蘭卻不肯罷休了,扯住希昭的袖子說:嬸嬸要不說出實情,絕不放手!這一刻又好像回到往昔,蕙蘭做姑娘的日子,有多少時光與事故來了又去了,希昭的鬢腳約略見白,蕙蘭呢,素衣素裙,煢煢孑立。兩人相視一眼,不約而同有一股傷感,蕙蘭鬆了手。希昭說:是真的好,虧你想得出,也繡得出,堪稱世上一絕!蕙蘭不相信:是真的嗎?希昭說:什麼時候說過假話?不過——蕙蘭心裡一緊,怕就怕「不過」兩個字!希昭說:不是讓道實情的?蕙蘭一閉眼,横下性命似的:說吧,说說吧!
希昭說:畢竟太過刁鑽了!蕙蘭睜開眼睛,看著希昭,這話幾有振聾發聵之勢,已不止是好和壞的意思。希昭說:多少有些炫耀,自然讓世人耳目一新,然而,终究不是大道。蕙蘭此時心平氣和,嬸嬸的話字字入耳:髮繡果然有蘊含,因是受之父母,又是身體氣血,用於言志明心,可寄託寓意,但到底是在繡外,走的是偏鋒,偶爾為之尚可,不能成氣候!蕙蘭惟有點頭。希昭接著說:技藝這一樁事,可說「如履薄冰,如臨深淵」,稍有不及,便無能無為;略有過,則入「雕蟲」末流!蕙蘭這才開口,疑惑道:如何才能不偏不倚居正中?希昭笑道:這就不好說得很了!沉吟片刻,又說:大約要牽涉到繡之外了,不止是針線的事,天香園繡與一般針黹有别,是因有詩書畫作底,所以我常說,不讀書者不得繡!蕙蘭臉紅一下,想到私下傳授於民女婢女,不由阻斷希昭話頭:方才說髮繡偏入繡外,此時又說天香園繡也涉及繡外。都是繡外功夫,應是如出一轍!希昭嘆道:所以我說薄冰與深淵呢,這一轍不是那一轍,南轅北轍就是從此得來!先頭說的那繡外,是在技;後頭的繡外,則在心!
蕙蘭「哦」一聲,似有領悟。停了一時,喃喃自語說:嬸嬸的意思是先養心,方學技。希昭亦沉浸在思緒中,兀自說道:都知道天香園繡好,誰又知道天香園繡中有多少心事呢?你大伯祖母先要希昭學繡,其實萬般牴觸,後來幾乎是,看見大伯母就要繞道走,從小讀了些書,自視不是女紅中人,多少妄自尊大!希昭輕笑一下,笑自己年少時的輕薄,哪裡知道箇中深淺。日頭偏了,庭院裡的光和影都移了地方,徐徐地,互相錯著,錯著,然後停住,又有一長段的靜止不動。蟲啊,鳥啊,都在午眠。希昭看蕙蘭一眼:你知道咱家從誰開始這繡的?蕙蘭懵懂地望着希昭,她還以為天生就有。希昭說:其實是從閔姨娘 起始的。閔姨太?蕙蘭眼前悄然浮起一個細瘦白皙的身影,坐於角落裡的窗下。埋頭在花繃。極少聽見她言语,甚至都難得與她照面,卻有一雙手,一上一下,遞針接針,轉眼間,一片彩雲,一泓流水,一朵花,一株草,顯現綾面上。真不敢相信,蕙蘭說。希昭耐心道:你看繡藝啊!閔姨娘的繡藝是最上乘,那些行針,辟絲,其實全出自閔姨娘的傳教。那閔姨太又從何處得藝?蕙蘭還是不甚相信。希昭老實說:這就不得而知了,大約是蘇州,蘇州向有衣被天下之盛名嘛!莫小看草莽民間,角角落落裡不知藏了多少慧心慧手。只是不自知,所以自生自滅,往往湮没無跡,不知所終。蕙蘭「哦」了一聲。希昭說:大塊造物,實是無限久遠,天地間,散漫之氣蘊無數次聚離,終於凝結成形;又有無數次天時地利人傑相碰相撞,方才花落誰家!要追根問柢,恐怕一無所得,只好從有形之時說起。蕙蘭同意:好,那就從閔姨太說起!
希昭接着說下去:閔姨娘將繡藝帶來咱們家,倘不遇上大伯母 ,大約也就止是個針線女紅,無非是略精緻華美一籌,可大伯母卻是書香中人——說到此,希昭不免羞紅臉:年輕時不知天高地厚,只當自己讀過幾本書就當得上書香,豈不知山外有山,天外有天!莫看上海不過是商瀆之邦,幾近荒蠻,可是通江海,無邊無際,不像南朝舊都杭州,有古意,卻在末梢上,這裡是新發的氣勢,藏龍卧虎,不知有多少人才!你大伯母可是有淵源的,據說年輕時,大伯父納娶閔姨娘。大伯母心中鬱悶,作過璇璣圖,如今不知藏哪裡了,要我作可作不來;閔姨娘的繡藝裡掺摻入大伯母的詩心,就更上一層樓;除去這兩位,還有一個人,也注入過心思。誰?蕙蘭問。這個人你没見過。我也没見過,卻與你我都有親缘,就是我的婆母,你的親祖母!蕙蘭「啊」一聲,方才想起自己是當有一個親祖母的。希昭說道:極早的時候,她便去世,在世時,與大伯母最知心,閔姨娘也得她照應,是極為大度善解的一個人,若不是她,只怕大伯母和閔姨娘到今天還不說話,也談不上有什麼「天香園繡」了!她入殮時的裝裹,是閔姨娘與大伯母親手所繡,據家中老僕人說,此生此世,再不能有如此絕品,艷到慘處!可惜你我都無缘看上一眼。
此話說罷,兩人又是沉默,院中花影再移一回,又不動了。東屋裡悄無聲息,好像也在側耳聆聽。希昭說:所以啊,天香園繡中,不止有藝,有詩書畫,還有心,多少人的心!前二者尚能學,後者卻絕非學不學的事,惟有揣摩,體察,同心同德,方能夠得那麼一點一滴真知!蕙蘭說:那些人,都是錦心繡手,可是嬸嬸,你也是天香園繡裡的添磚加瓦人,繡畫就從你起始!希昭笑道:究其柢還是藝,至多沾一些書香氣,前輩人的心事心知,與咱們隔了不知多少層。蕙蘭說:可嬸嬸集前輩人之大成,青出於藍勝於藍,推天香園繡而至鼎盛!希昭說:那也是時運,好比種桃,一茬青,一茬黄,終於熬到一茬紅熟,巧不巧從樹底下過,落進懷裡!蕙蘭說:樹底下過的人多多少,還是要個有緣的才能得,這就叫作知遇之恩呢!希昭聽見這話,倒是一愣,出會兒神,慢慢地說道:據說咱家園裡的桃林,當年幾可賽得過天上王母的蟠桃會,可一茬不如一茬,再經過無數次扦枝,不得已便枯萎下來,如今索性都不掛果了。蕙蘭說:可到底是傳開了,南門外,還有松江廣富林,都已成林,市中沽賣,最搶手的還是它們!希昭說:究竟不如最初,根子裡生出來的,好東西都不經多,一多便稀薄了。說到此,蕙蘭心裡暗暗一驚,覺著嬸嬸希昭影射她授教的事,可希昭並未把話說下去。
停一會兒,蕙蘭說:以後再不做這髮繡了。希昭笑了:何必如此沮喪,這髮繡自有一種肅然,在米白絹面上,切切懇懇的,於佛像倒十分貼合,但終是比不上絲啊!那絲是蠶吐命一般吐出來,經無數雙手調治,方才有它;那髮就過於現成,本不是用作針線,物各有用途,也是物裡的德性吧!蕙蘭說是,卻又不服,抬頭問道:那麼以繡作畫,難道不是物作他用?將針作筆,將絲作墨,算不算作偏鋒?希昭又一怔,說:我倒是被你問住了!蕙蘭得意地一昂頭,揚眉吐氣的樣子。希昭一邊想一邊說:繡與畫許是前世一家,繡就是畫,畫就是繡,陰差陽錯,分為兩家,再又幾度輪轉,陰陽遇合;好比觀世音是男女同身,到了凡問眾生,才分為男女,需修煉幾百幾千世,又可合二為一;畫人說「墨分五色」,大約就分到絲裡來了;書人所說「筆鋒」,其實是指「針」吧!所以,繡畫亦還是遵循物理,不脱原意!蕙蘭聽此說法,大覺有趣,興奮道:上古時候,天地混沌一團,自盤古開天地,各歸其位,各司其職,方才有了五行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!希昭亦很興奮:然而五行相生,五行相克,終為一體;又好比春秋戰國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!蕙蘭忽又冷靜下來:如此說,髮繡是在五行之外?希昭再是一怔,方才明白的事理,猝然間又被說亂,斥道:怎麼又扯上髮繡不髮繡的,正在說世間萬物呢!蕙蘭堅執要問:髮繡究竟該算在哪一門裡?希昭說:哪一門都不算,歪門邪道!蕙蘭道:你說的?希昭道:我說的!兩人撕扯纏磨的勁頭,又回到從前。鬧了一陣,希昭說:無論是不是正道,這髮要辟成絲,也算得一絕技,只是無關乎繡!提到辟髮,蕙蘭不禁畏縮起來,住了嘴。
希昭並未覺察蕙蘭的遲疑,繼續說道:絕技是絕技,然而究竟是單一的用物,除去線描,難作别用,這也是物性所限。蕙蘭小聲道:可是,這髮繡確有我蕙蘭的心在。希昭注意地看蕙蘭一眼,忽覺著一股剜心般的痛楚,緩和了口吻道:我很知道,我們這不是在說繡藝嗎?這物性多少是狹隘了,只拘泥於物本。蕙蘭問:哪樣物不是拘在物本裡,否則,何為此物。又何為彼物?希昭說:物有大小之别,小物只一生一,二生二;大物則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萬物!不可等量齊觀。蕙蘭又問:比方說呢?希昭說:天,地,人,這三件本是造化,無從論起,凡議論都是犯上,單就說些常見常用的東西——螢火蟲,只一夜生息,亮過即滅;蜜蜂,生長之後,採蜜釀蜜,蜜可食,又可製蜂蠟照明;再有一年生的草本,僅一歲枯榮,回進土裡;而常年的果木,先生葉,後開花,又結果。饗食人間;還有石,可煉鐵,鐵可製鍋釜,鑄劍,鑄鼎,鑄鐘,可祭天地!物性就好比物之德,有大德,亦有小德,甚至無德;咱們閨中的針黹,本是小物小德,但卻是有淵源的,淵源是在嫘祖。與黄帝齊輩分——聽到嫘祖兩個字,蕙蘭心頭怦然一動,神情就有些異樣,希昭不免看她一眼,蕙蘭定了定,聽嬸嬸說話:因是源遠流長,所以就能自成一體,自給自足,可稱完德,無所而不至。希昭停下話頭,對了蕙蘭,無盡地體貼與同情,緩緩說道:髮繡確是有你心在,可只在膚表,距深處還遠得很!
蕙蘭點頭。希昭說:一件物,倘若物表、物性、物本皆全而美,且又互為照應生發,便是上乘,缺一則不成大器。蕙蘭笑道:聽嬸嬸說來,都無法正眼看這髮繡了!希昭也笑道:不過是借題發揮,信口開河,凡繡成的,便已立於不敗之地,算得上功德圓滿!還是要說,辟髮是天下絕技,難為想得到,又做得成。蕙蘭心情已復平靜,坦言道:辟髮是戥子所為。希昭略想一想,不禁笑道:就是那個小丫頭?粗粗拉拉的。蕙蘭說:看上去是個粗人,可一雙手格外的巧。希昭說:那就是天賜了。蕙蘭又說:這些人就像路邊田間那類没有姓名的稗草,嬸嬸方才說的。渾然不自知,但其實,也有她們的心事。希昭收了笑,認真聽起来,蕙蘭便一逕說下去:嬸嬸你看那些野花,無論多麼小或者賤,不過半日,便又化進地裡作了泥。可也有薄如蟬翼的瓣,纖長细緻的蕊,頂著一丁點兒的蜜,供蜂們去採集,那就是它們的心事吧!這些心事或都是粗鄙的,免不了爹死娘嫁人,或者缺衣少食一類的苦楚,可也是心事一樁,到底是女兒家。未出閣的,乾乾淨淨,就能將那些苦楚打磨成女兒心!再給嬸嬸看一件東西。蕙蘭說罷返身走下院子,進自己屋裡,將希昭一個人留在廳堂。
院裡的樹影一動不動,其實没過去多少時間,半個時辰最多,卻像過了一世,翻山越嶺,都望不見來路似的。正出神,樹影中走来了蕙蘭,手裡捧一卷綾子,當希昭面前展開。米白綾面靛藍絲繡,「晝錦堂記」四個字題額,底下有二三行繡成,其餘還是炭筆所描字跡。那繡成的題和字,點頓撇捺,折轉斷續,猶如行雲流水,既有筆墨意趣,亦是絹秀格調。蕙蘭說:嬸嬸知道她們怎麼說?怎麼說?希昭問。她們只當這是草葉花瓣,絲練纓絡,或是燈影燭光,勿管字不字的,又勿管寫的是什麼,只覺得出神入化!希昭端詳一時繡字,說:你說「她們」是什麼意思,難道除戥子外還有别人?蕙蘭知道今天是挨不過了,既已開頭,只有和盤托出:還有一個妹妹。
蕙蘭將乖女 的身世來歷一五一十說了一遍,希昭不作答,只是默著。蕙蘭道:我自己都没學好。怎敢收徒,只是她們真心想學,又實在可憐,一生無所託寄,倘有一技在身,或可自食其力,糊個口吧!希昭淒然一笑:天香園繡竟要用於「糊口」!蕙蘭說:若大伯祖母與嬸嬸不答應,萬不許落天香園款!希昭又是淒然一笑:我是不在意的——蕙蘭道:可大伯祖母她——你大伯祖母多少糊塗了,希昭說,你知道,昨日裡她老人家叫我什麼?叫我「閔女兒」。「閔女兒」就是閔姨娘。蕙蘭說:那是因為嬸嬸和閔姨太是天香園繡中最好的。希昭說:落不落款又算得上什麼,天香園其實早已凋敝,空留個繡名!蕙蘭說:要我看,天香園繡很對得住天香園,那草木樓閣說朽就朽,繡品可是口口相傳,代代相傳,所以,那繡藝千萬不能讓它滅絕了。希昭看蕙蘭一眼,說:早聽說你開門授徒,卻不知道於天香園繡是損是補!蕙蘭苦笑道: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,早晚申府都會興師問罪,果然,嬸嬸來了!希昭說:並不是問罪來的。蕙蘭固執道:就是問罪來!蕙蘭我膽大包天,取天香園繡名做妝奩已屬出格,又要傳於坊間,毀天香園清譽!希昭說:是夠大膽的,但事已做下,問罪如何,不問罪又如何?我只好奇,收了些什麼樣的學生。有無造詣!
蕙蘭說:雖是背了天香園私自收徒,卻也不逾矩,拜了嫘祖!說到嫘祖,兩人相視一眼,會心而笑。蕙蘭再接著說:就按童子開蒙的式子,略改了改,變寫字讀書為繡活,亦是借用七月七乞巧會的沿習,所收這兩名,又均是鐵定心不嫁人,不出閣,一是免去濫傳之虞,二也是不至過於受生計之累,最終蹈入沽鬻衣食,棄道背義!希昭不覺點頭:你這丫頭倒是正經設帳了!蕙蘭正色道:可不敢有半點疏忽,這是樁大事情!希昭說:明知道大事情,還先斬後奏!蕙蘭一屈膝,跪下了。希昭說:起來,起來,最見不得這個!蕙蘭很害臊,起來了,卻手足無措,只低頭站著。希昭說:別看你又下跪又低頭,其實心裡有諸般的不服氣!蕙蘭說:不敢!還說不敢?蕙蘭就說:敢!希昭拍一下案子:把你的爪子剁了!嬸侄二人又戲謔起來。鬧一陣,希昭歎一口氣道:大伯母已老了,我也半老,你呢,終也有老去的一日,再是捨不得的東西,握也握不住,隨波逐流罷了!蕙蘭聽見此話倒上來脾氣了:再怎麼隨波逐流,武陵繡史還是武陵繡史,怎麼也抹不去的!希昭苦笑道:這武陵繡史又像是我,又像是與我無關,如今,沒有一幅繡畫留在手裡的,都天南海北,不知在了什麼地方!蕙蘭說:無論天涯海角,總是在人世間!希昭又說:還是散出去乾淨,這天香園早晚夷為平地,申府又能有多久,哪裡會有千年不散的筵席!
兩人靜一靜,蕙蘭道:有一句話,說又不敢,不說又可惜,再想,豁出去說了吧,至多——希昭問:至多怎樣?蕙蘭說:嬸嬸罵我!希昭譏誚道:跪都跪過了,還怕罵嗎?蕙蘭說:嬸嬸去看一眼如何?不等希昭說是或不是,蕙蘭緊接著又說:也不能全怪我冒昧,是嬸嬸自己送上門來的,豈能放過呢!希昭又笑又氣:怎麼叫作「送上門來」?到侄女兒家坐一時,喝一盅茶,難道逾矩了?蕙蘭聽出「逾矩」這兩個字的來歷,分明是借用方才說拜嫘祖的話,無論怎麼冷嘲熱諷,反正今天嬸嬸是脫不出身了。蕙蘭也抱定一不做二不休,極力地慫恿,將那兩個說得花一般的。由不得希昭不動心。將手裡的茶盅放下,一起身說:看就看,長點見識,不定是天上哪一個星宿!蕙蘭上前一步擋住:要說星宿,嬸嬸才是,我是得了惠顧。那兩個卻是草根裡最苦的一味,竭力強掙著,或可吐一點芬芳,求嬸嬸寬待!希昭定定地看蕙蘭一眼,抬手輕輕將她撥開,出廳堂,下臺階,向東屋走去。
日頭偏西,院子被切成兩半,一半光,另一半也是光,卻是從影裡透出,罩著一張網似的,不是模糊,而是寧和。推開門,門裡的人一起抬頭往這邊看。希昭不由一驚,那露在面罩上邊的一雙眼睛,還有戥子,平日裡從不注意,如今才發現她亦有一雙杏眼。從亮地裡進到屋內,陡地一暗中,那四隻眼睛顯得極清明,還有一種肅然。因為猝不及防,又因為敬畏,這兩個都忘記起身,只是望著希昭,傳說中的武陵繡史。漸漸適應屋內的光線,那些眼睛裡的光也柔和下來,身子動了動,要起來行禮,被希昭止住。走到花繃前低頭看繡活,不料先看見一個小竹床。床上睡一個嬰兒,也有一雙明澈的眼睛,同樣是肅然的,但因是嬰兒,就比大人更為逼人。希昭停了停,忽覺這間屋裡有一股凜冽,從四角上下聚攏來,心裡暗問道:這是什麼呀!定定神,希昭彎腰看那蒙面女的繡活,那針法都是從天香園繡來的,循規蹈矩,但看起來卻又不盡相似,仔細辨認,發覺差別是在用色。每一種色都要厚重一成,是辟絲不夠細分,還是有意為之,抑或二者皆有?希昭思忖一時,心中猶豫。如此用色,自有著強勁迸發的意蘊,於天香園繡的清雅倒是有另一派新鮮,可難免又粗疏了,稍有差池即落入鄉豔。希昭再又細辨幾番針法,才抬頭與蒙面女說出癥結:用針堆砌了!那女子「哦」的一聲,已是領悟。然後到戥子跟前。戥子比那一個學天香園更像,要不是針下禽鳥有一股野趣,幾可騙過希昭的眼睛,不禁笑道:比市裡那些贗品還更像些呢!眾人也都笑了。希昭看出這一個比那一個會仿,但不如那一個有主意,心思深。這一個至少不會貶損天香園繡,那一個卻不定會有如何的新進和錯接,將天香園繡引向什麼樣的去處!
希昭從花繃上起身,四下裡亮晶晶的眼睛都含了笑意,幾乎開出花來。光線更勻和溫潤,潛深流靜,這間偏屋裡漸漸充盈欣悅之情。希昭想起天香園裡的繡閣,早已成殘壁斷垣,荒草叢生,不想原來是移到坊間雜院,紆尊降貴,去盡麗華,但那一顆錦心猶在。那兩個站起身,直直地鞠下躬去,蕙蘭在前邊推開門。院裡地上花影團團,希昭走了進去。(節選自p505-516)
教學小建議(此書可搭配《紅樓夢》進行教學)
1.教師可就上列文本提出以下討論問題:
(1)請學生說出本章節出現之人物,並請學生進行人物關係之說明。
(2)沈希昭與申蕙蘭對繡藝的看法有何不同?請以條列方式分點列舉。
(3)沈希昭與申蕙蘭的對話,有何言外之意? 哪一段讓你感觸最深?
(4)對戥子與乖女等下層社會女性而言,天香園繡讓他們有什麼樣的生命意義轉變?
你認為王安憶想傳達的是什麼信念?
2.就內容而言,《紅樓夢》所描摹的年代與《天香》幾乎是重疊的,兩者也同樣以世家大族的沒落為背景,但曹雪芹和王安憶在結局的安排上有極大的不同。教師可引導學生在假期進行《紅樓夢》與《天香》文本的閱讀,並比較兩位作者在結局安排上的深意(可以用小論文方式進行)。
3.老師也可介紹民國以來京派、海派小說的發展史,並說明海派小說在當代的影響力。
教學文章由北一女中 蔡永強老師提供
王安憶的母親茹志鵑,無疑地在女兒的血裡投下了一顆巨石,排空的熱血浪濤,使得王安憶成為一個女性意識極為強烈的作家,女性的韌性,就如繞枝的葛藤,牽繫著作品的靈魂。早期《處女蛋》中的阿三,墮入迷惘而淪落的困境,代表的是一群身陷濃霧中的民族女性;改編為電影的名作《長恨歌》,文本中女主角王琦瑤,就像一卷當代女性的風情畫,隨著王安憶的手捲開長軸,我們睇見了時代風雲中女性自我生命實踐的步履;溫婉剛毅的《富萍》則是首動人的歌謠,一個從農村躑躅到上海的女子,拋棄唾手可得的物質富貴,採摘了雖艱難卻甘美的真愛果實;家史小說《紀實與虛構》中,王安憶追溯的是母親茹姓的洪荒過往,女性圖譜的建構,除了是王安憶自身血緣身分的確認,更是自我女性空間的打造。
《天香》一書中,王安憶表面是寫一方如《紅樓夢》大觀園的天地,申家男女的歡愛與憎恨在園裡蔓衍糾葛。骨子裡王安憶卻將申家女性的突圍繡在了文字裡,無論是愛情的困境還是物質的困境,申家女性既像鋼針又像棉線,自能繪繡出上海的軟語多情,他們更引領著閭里無靠的女性,一針又一針地往外繡,繡出一幅天寬地闊的世界。誠如王安憶自己所說的:「說到底聲色犬馬的一切,我是喜歡的,它是道德之外的一個世界。」申家天香園的女性,正是在聲色犬馬之中找到自我的一縷幽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