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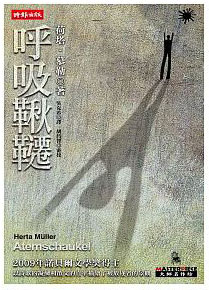
荷塔.慕勒(Herta Muller)德國小說家、詩人、散文家,於200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慕勒1953年出生於羅馬尼亞的尼慈基村,自1987年起喬遷德國。德裔出身的慕勒,早年曾經生活在羅馬尼亞的專制政體下,因此作品經常帶有政治色彩,生動描寫出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專制政治的影響和控制,而長於詩歌創作的她,詩性的文字實驗亦備受推崇。
慕勒主要是用德文寫作,多部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等。除了《呼吸鞦韆》(Atemschaukel)外,慕勒另著有《風中綠李》(Herztier,1994)、《狐狸當時已經是獵人》(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ager,1992)、《衛兵拿起他的梳子》(Der Wachter nimmt seinen Kamm,1993)、《今天我不願意面對自己》(The Appointment)等書。
《呼吸鞦韆》一書,描寫二戰後1945到49年蘇聯勞改營裡一群德裔羅馬尼亞人的故事。他們被送到了勞改營,替希特勒的德軍贖罪,幫俄國做戰後重建,成為二次大戰後時代的犧牲者。在勞改營中,隨時都可能發生逮捕、酷刑或謀殺,恐怖的陰影彌漫在日常生活中,尤其是時時刻刻的飢餓狀態,讓人無處可躲。慕勒以一種獨特而帶有詩意的筆觸,讓作品在自然中滲透出一種窒息的恐怖感,藉由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直率,描繪了一幀幀被放逐者的景觀。(改寫自博客來網站2017.02.14 http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515604)
黑楊樹
那是十二月三十一日跨入一月一日的夜晚,第二年的新年除夕。我們半夜被廣播器叫到集合場上去。八名荷槍士兵牽著獵犬,從營區街道兩側趕著我們前進。一輛卡車跟在後面。我們被帶到工廠後面厚厚的積雪中,那裡再過去就是荒地了,大家聽令列隊站在砌起來的圍籬前等著。我們心想,這是槍決之夜了。
我擠著排到前面去,好早一點被解決,省得在受刑前還要搬屍體──因為那台卡車就等在路邊。西西特凡紐諾夫和徒爾.普里庫力奇爬進前座,馬達開著,以免他們凍著了。戒護兵來來去去。警犬擠在一處,霜氣壓得牠們的眼睛都閉起來。牠們不時抬一抬爪子,免得被凍僵。
我們站在那裡,一臉蒼老,眉毛掛著白霜。有些女人雙唇打顫,不只是因為冷,還嘟噥著祈禱。我告訴自己,現在一切都要結束了。我祖母的告別話是:我知道,你會再回來。儘管那時候也是午夜,但畢竟還是置身於世界之中。他們現在在家裡慶祝除夕,子夜時也許會舉杯為我祝福,祝我活下來。但願他們在新年一開始的幾個小時裡會想到我,然後再鑽進暖暖的被窩。祖母的結婚戒指已經擱在床頭櫃上了,她每晚都會拔下來,因為箍得不舒服。而我卻站在這裡等著被射殺。我看到大家都站在一個巨大的盒子裡。它的天蓋被夜晚塗上了黑漆,點綴著磨得鏨亮的星星。盒底鋪了一層膝蓋深的棉花,好讓我們綿軟軟倒下去。盒壁上掛著硬邦邦的冰霜織錦,絲綢般的撩亂流蘇和蕾絲,無邊無際。營區圍牆再過去, 看守塔之間積雪正好充當靈柩台。台上聳立著一座高塔式的疊床,直指天際,那是一座塔樓棺槨,我們每個人的靈床層層相疊,如同寮房裡的床架一般。頂層再蓋上烏漆棺蓋。靈台頭尾處的看守塔裡,有兩位尊貴的黑衣人在守靈。靈台頭端指向營區大門,大院裡的看守燈閃閃爍爍,宛若燭台。稍暗的靈台尾端立著罩雪的桑樹樹冠,彷彿一把華麗的花束,上面無數的小紙片寫著每個人的名字。雪會吸音的,我想,射擊幾乎聽不見。我們的親人在世界之中微醺入眠,帶著除夕的疲憊,了無罣礙。也許在新的一年,他們會夢見我們被魔法詛咒的葬禮。
我再也不想從這個塔樓棺槨的盒子裡走出去。人一旦想克服他的死亡恐懼卻又無法逃脫時,它就會變成迷惑。冰寒也是如此,如果人在其中動彈不得,嚴寒就會吐出絲絲的溫和。在凍僵的恍惚之中,我把自己獻給了槍決。
但是接下來,兩個裹得暖暖的俄國人卻將卡車拖車上的鐵鍬丟到我們腳跟前。徒爾.普里庫力奇和其中一個暖裹兵,在黑暗和雪亮之間拉了四條打了結的繩索,和工廠牆腳平行。西西特凡紐諾夫司令已經坐在駕駛艙裡睡著了。也許他喝多了。他下巴堵著胸口,像一位被遺忘在終點站車廂裡的旅人。我們鏟了多久,他就睡了多久。不,他睡了多久,我們就鏟了多久,因為徒爾.普里庫力奇還得等他下令。我們在繩索之間為自己的槍決挖開兩道溝,他則呼呼大睡。我不知道挖了多久,直到天空濛濛亮了起來。我一直跟著鏟子的節奏重複:我知道,你會再回來。我已經從鏟雪中清醒過來,我寧可繼續為俄國人挨餓、受凍、做牛做馬,也不要被射殺。我認同祖母說的:我會再回來,然而另外一句卻在唱反調:但你也知道的,這有多難。
接著西西特凡紐諾夫從卡車前座下來,搓了搓下巴,抖一抖腿,或許因為兩隻腿還在睡。他示意要那兩個暖裹兵過去。他們打開車子的尾板,把鶴嘴鋤和鐵撬桿丟下來。西西特凡紐諾夫用食指比來比去,不尋常地說得又短又輕。他又爬上駕駛艙,空車載著他揚長而去。
徒爾必須為司令的咕噥渡上一口命令語氣,大喊一聲:挖樹坑。
我們在雪地上找工具就像在找禮物。地上凍得跟骨頭一樣硬。鶴嘴鋤敲下去彈起來,鐵撬桿響得像鐵打鐵。核桃大的土塊彈到我們臉上。我在寒霜中流汗,又在汗水裡挨凍。我整個人崩裂成火半截和冰半截。上半身烤焦了,機械性地向前彎,擔心無法完成配額而焦灼不已。下半身卻凍僵了,兩隻腿冷冰冰地插進腸子裡。
到了下午,雙手已經血肉模糊,樹坑卻還沒有一掌深。它們就這樣留著了。
樹坑一直要等到晚春才挖好,種上兩排長長的樹。林蔭大道長得很快。這種樹其他地方沒有,草原上沒有,俄羅斯村或附近任何地方都沒有。整整好幾年,營裡沒有人知道那種樹叫什麼名字。它們長得越高,枝枒和樹幹就顯得越白。不像樺樹那般銀絲纖細,蠟白通透,而是樹體雄偉,樹皮如石膏糊般了無光澤。
從營裡返鄉後的第一個夏天,我在艾爾連公園看到了這種石膏白的營樹,古蒼而巨大。我叔叔艾德溫的樹木百科裡寫道:此一生長快速的樹種,可射向天際達三十五公尺高。其幹可粗至兩公尺,樹齡可達兩百年,足證此樹之堅韌。
我叔叔艾德溫不會瞭解,當他對我念出射字時,這形容多準哪,簡直就是一語中的。他說:這種樹很容易活,而且特別漂亮。不過這裡有個瞞天大謊。為什麼它樹幹是白的,卻叫做黑楊樹呢?
我沒有反駁。我只是在心裡想:人如果曾在漆黑的夜空下,過了大半夜只等著被射殺,那麼這個樹名就不再是瞞天大謊了。(節選自《呼吸鞦韆》頁66-69)
教學小建議
1.陳列的《地上歲月》一書,展露了作者自出獄後致力筆耕的心境,其中的〈無怨〉一文,展現了陳列在雷雨聲中回顧獄中情懷與重建自我的體悟。教師在教授陳列的文本時,可補充荷塔.慕勒的作品,讓學生能更深切了解:專權政治之下,人性是如何的被扭曲與自我救贖。
2.請閱讀下列羅毓嘉的〈黃溫恭〉篇章,試分析慕勒的〈黑楊樹〉與羅毓嘉的〈黃溫恭〉在寫作筆法上有何差異?這樣的差異會形成什麼樣不同的文學效果?
黃溫恭(節選)
這是他生命最後,最為短暫又漫長的午夜時分。
僅能疾書,僅能振筆,黃溫恭逐一寫信給自己結縭六年的髮妻,乃至小姨、稚子與幼女,他那尚且未能謀面的么女,他懇切地想要擁抱、親吻一回的么女。只剩幾個小時了,該怎麼好好訴說自己的想念。他想像著,想像著自己的大兒子能成為鋁一般有用的人才,會成為土木工程師,而那有著絕佳音感的長女,可能成長為有名的大音樂家嗎?至於么女,自己未曾相見的女兒,那兩張襁褓中的照片是他思緒為一所能寄託之處,他看著她白胖的面頰,身為父親的片面遐想,她若能成為獨當一面的律師,該有多好。
這些幻想如露如電,孩兒們的形影轉瞬就要消逝。不知過了多久,他的指掌已因久握鋼筆而僵硬,日漢交雜的字跡,也愈呈紊亂。
先前的通信裡邊,妻要他臨刑前穿上球鞋,要他,切莫忘記把手放進褲袋。如此,即使屍身面孔模糊,家人領屍時也能很快認出他來。可他不希望這樣。在給妻的遺書裡,他寫道,屍身不可來領。別來領。他想,這塊土地——這亂世中的土地——還需要更多濟世的醫師,而倘若這具屍首能捐贈予臺大醫學院或其他的醫事人員訓練機關,當能讓學生們做大體解剖,習得更多的知識。先前,在獄中落下的兩顆牙齒已寄回家裡,在他口腔裡留下陰惻惻的空洞,那就是他的遺體了,就當作是他遺體的全部吧。(節選自羅嘉毓等合著《無法送達的遺書: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》頁84-85)
教學文章由北一女中 蔡永強老師提供
